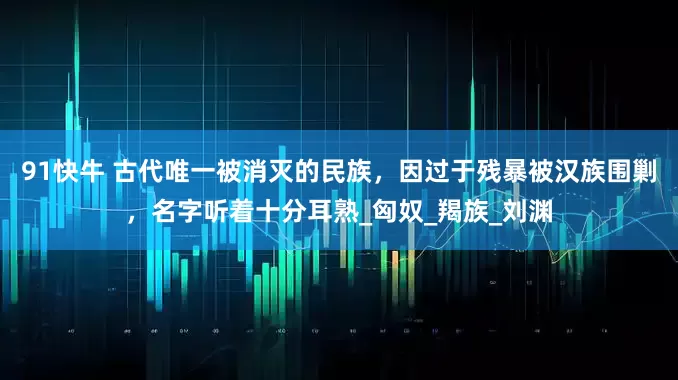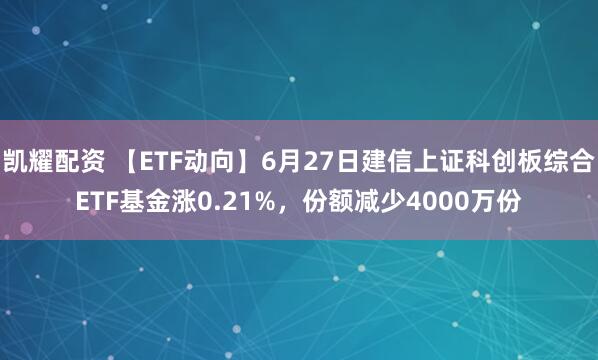杜聿明在《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述略》(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抱怨:“中国远征军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罗卓英把军队的‘生地’变成‘死地’,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拾贝赢,丧师辱国。我最大的责任是1942年4月19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
杜聿明表示:“对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我可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的命令,未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
当时的杜聿明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手下有第五、第六、第六十六三个军,他穿越野人山尚且遭遇“惨境”,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有多惨,那就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了——时任第五军政治部上尉干事的李明华是四十名女军人仅剩的四名幸存者之一,她的回忆文章《野人山历劫记》,现在看来,还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有资料说当年第五军只有一位护士班女兵刘桂英,那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份史料中并不包括后来没留在大陆的幸存者。
李明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零二辑中发布的《野人山历劫记》写得很清楚:“当时计有第五军军部、军直属部队和新编第二十二师,总人数约在一万五千人左右,而最后越过野人山到达印度者只有三四千人。当时随军部撤退的女同志除战干一团女同学胡汉君和我两人外,还有政工队女队员和几位眷属,共约四十多人,最后到印度的只有四人。胡汉君和我是劫后余生者。”
李明华只是上尉,自然没法跟副司令长官兼军长杜聿明一路同行,杜聿明向沈醉回忆他穿越野人山时的艰苦,看起来还不及李明华遭遇的千分之一——李明华和她的女战友们,每一秒都面临死亡,而杜聿明的境况,在他看起来艰苦,在李明华看来那就是“幸福”。
杜聿明是这样对沈醉说的:“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区是从来没有人深入到里面去过的,更不用说要穿越它了,走在前面开路的是六头大象,用鼻子卷着锋利的缅刀,把一些藤葛劈开,好让人鱼贯通过。”

杜聿明手下有兵有枪,还能猎杀大蟒烧烤,并因烟雾引来美军空投:“这是森林中最佳的美味了,不料升起的缕缕炊烟,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了拾贝赢,便立即在上面盘旋,并向基地报告了发现的情况。飞机不敢飞远,怕回头找不到这一小块升起炊烟的地方。很快两架早就做好准备的小型运输机飞来了,向这一小块空地上投下了电台、粮食、医药等。”
与杜聿明的有吃有喝有药品截然不同,李明华和她的姐妹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杜聿明已经下令军部毁掉全部重武器、装备、车辆,所有人徒步进入野人山:“初时队伍还能像蚂蚁队伍一般一个接一个前进,几天后就渐渐分散成三三两两的散兵游勇了。断粮半个多月,人人饥饿疲惫不堪,连当天是几月几日都无力记忆。当时国军未曾有过野外求生训练,第五军也未实施过山地与丛林作战训练,很多官兵因饥不择食,吃了有毒的野菜而丧生。”
杜聿明的第五军也算远征军王牌部队,但即使是这样的王牌,也没有经过野外生存训练,难怪在撤退途中损失惨重,杜聿明后来统计损失,给出了一串冰冷的数字:第五军直属队一万五千人,战斗死伤一千三百,撤退死伤三千七百;二百师九千人,战斗死伤一千八百,撤退死伤三千二百;新二十二师九千人,战斗死伤两千人,撤退死伤四千人;九十六师九千人,战斗死伤两千两百,撤退死伤三千八百。总价四万二千人,战斗死伤七千三百,撤退死伤一万四千七百。

杜聿明在《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述略》中给出的这一串冰冷数字令人愤怒:每个师怎么会不多不少正好九千人?这里面有没有漏报和吃空饷的?为什么撤退死伤人数是战斗死伤的二倍之多?杜聿明有大象开路、卫兵保护,基层军官和普通士兵为啥没人管?
杜聿明已经顾不得部下死活,女军官和护士们更是很少有人顾及,但是在残酷而冷漠的战场上,也有人性的光辉和军官们的卑劣行径。
李明华亲眼看到战友吃了野芋和野芭蕉根全身浮肿而亡,因此我和胡汉君只能天天用大叶子接些雨水充饥——溪水因为浸泡了太多的腐尸,早已不能饮用。
断粮半月的李明华互相扶持,她们没有枪支弹药可以像杜聿明的卫兵一样狩猎,就只能到猴子窝里找野果子吃——她们也没经过野外生存训练,自然分不清哪些果子有毒,但猴子能吃的,应该没有问题。
在生死关头,有些战友情已经丧失殆尽,尤其是国军军官,更是不拿部下当兄弟拾贝赢,于是李明华遭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无情打击:“远远望见一座芭蕉棚,精神为之一振,急忙加快步子赶去,渴望就近火堆取暖并烤干衣服。到达棚前,本科罗科长在里面,我如见了亲人一般地高兴,问了一声‘科长好’,马上将右脚迈进去。万没想到这平日慈祥而受人敬重的长官,一反常态手执棍棒,疾言厉色将我赶出棚外。”

干事是上尉,军部科长至少也得是少校,这个少校军官在生死关头,连部下进棚子避雨烤火的请求都用棍棒拒绝,其穷凶极恶,跟以往的道貌岸然想成绝大反差。
满腔悲愤愁怨的李明华只好远远避开,当时夜幕低垂,一条洪流湍急的溪水横在面前,胡汉君不知去向,李明华不敢一人渡河:“我一人静坐大树下,雨下个不停,双脚浸在半尺深的雨水里,肚子一直咕咕叫个不停,满脸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李明华肯定想起了她们投笔从戎时的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几个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考入“战时干部训练团”,毕业后又分配到前线,认为终于有了杀敌报国的机会,却没想到因为高层的勾心斗角、指挥失措,把这些大好青年都陷于绝境而不顾。
那个卑劣无情的科长,在危难之际不肯让部下分享避雨棚和篝火,自己也没能走出野人山。

李明华天亮后与觅食的胡汉君会合,在一位长者的帮助下跨过横木渡河(李明华失足落水,长者和胡汉君及时拉住),从后面赶上的华侨队丁队长和队员陈祈告诉他们:罗科长和另外三人已经死在溪那边的芭蕉棚里,我们们砍了四片大芭蕉叶将他们盖住了。
也不是所有的长官都像罗科长那样冷酷无情,同是战干团出身的杨纯少校就表现出了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
李明华和胡汉君遇到杨纯少校的时候,这位少校正躺在一间草屋外的空地上,他醒来后第一时间让李胡二人烤干衣服,并拿出仅有的一点面粉和糖,烧了一些面糊给她们吃:“每人分到半漱口缸。多日来未吃食物,觉得这面糊香甜无比,我两口就喝光了。他见此情形,又把他的半缸分给我们,粘在缸底的一层喝不到,就用指头刮出来吃,也全不顾什么礼貌、雅观了。”
杨纯少校并没有跟李明华胡汉君一同继续前进,而是把自己的两块甜饼分给了两位女战友一人一块:“大家同处在饥饿困苦的垂死边缘,杨大哥毅然将他的少许续命粮分给我们,握别时,我发现他手心很烫,知道他病得不轻,心中暗暗祈祷他早日恢复健康。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杨纯少校没能走出野人山,要不是李明华这篇回忆文章,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在那兵败势危的生死关头,还有像他那样肯牺牲自己救助战友的中级军官。
杜聿明和罗卓英谁该为远征军战败负责,这件事不太好下结论,但是看了李明华的回忆,我们却不能不想起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远征军激战丛林历劫野人山,多少好儿女埋骨他乡,这在杜聿明的回忆录中只是个模糊的数字:“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
两个不精确的数字,也反映了杜聿明的指挥能力,杜聿明回国后,负责“点检”的黄维也没给他好脸色,当时那场不愉快的见面,很多史料都有记载,咱们也没有必要过多纠结黄杜二人谁是谁非,读者诸君看了杜聿明和李明华的回忆文章,是不是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广升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